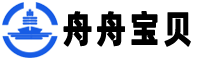“娘娘(祖母):您好吗?……侬寄的东西很好吃,谢谢侬!弟弟(我)有一百多个字认得了,有好些个字会写了……”
这是年6岁的周海婴写给祖母鲁瑞的信,这封被写得歪歪扭扭的信,鲁瑞反反复复看过,回信后,她还将信笺小心地珍藏起来了。

周海婴给鲁瑞的信
这样的信,有无数封,而这每一封信,无疑都勾起了鲁瑞对孙子的思念之情。可遗憾的是,鲁瑞至死,也未能见到已经14岁的周海婴。
祖孙至死未见,通常只有两种情况:一种是生死两隔,一种是断绝往来。可鲁瑞和周海婴却并不属于这两种,他们至死不得相见的背后原因,复杂且曲折。
幼年的周海婴并不知道:他出生前,父亲鲁迅原本和祖母住在一起。他更不知道,与他们同住的还有鲁迅原配朱安。自然,他对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也知之甚少。
周海婴的母亲许广平有意回避与朱安有关的任何话题,而鲁迅在信中也极少提及朱安,每次与母亲写信,他的开头都是:“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”,而结尾则总是:“专此布达,恭请金安。 男树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”。
经考证,鲁迅寄给母亲鲁瑞的120封信中,无一字提及朱安。可此间,朱安一直以“周太太”的名义,寸步不离地陪在婆婆鲁瑞身边。
鲁瑞越老越离不开朱安,自朱安嫁入周家起,鲁瑞的日常生活全由她照顾:朱安能做地道且符合鲁瑞口味的绍兴菜。为此,她曾数次向人夸赞大儿媳的厨艺。

中为鲁瑞;左为朱安
鲁瑞有多盼望儿子和孙子的信,她就有多想念他们。收到周海婴文首那封孩子体的信前,她就已经动了南下去探望他们的心思。
分外想念孙子的鲁瑞还想出了一个法子:请邻居俞芳带自己南下。打定主意后,她对俞芳说:
“他们(鲁迅、许广平和周海婴)来,一行三人,行动不便,还是我去上海好,我到上海可以看到老大、老三(周建人)两家人。”
之后,鲁瑞曾反复絮叨说:“见了面,该送什么见面礼呢?应该讲点故事给他们听,得把孙儿注意力引到娘娘这边,那样他们就都能腾出手来了……”
在一次听婆婆絮叨时,朱安终于忍不住开口了,她说:“路上远着呢,就你和她(俞芳)怕是不行!”
朱安的话终于把鲁瑞点醒了:她已经79岁了,这一去山高路远,她非得带个可心的人一起走才行。这个可心的人,当然最好是朱安了。
而朱安自己,也特别想南下,她一直想见见周海婴。她心里,一直将周海婴视为自己的儿子。她甚至还在周海婴出生后感叹:自己百年后,不会做孤魂野鬼了,因为有了海婴,他会给她烧纸、送羹饭、送寒衣……
朱安的心思,鲁瑞当然知道,她何尝不想带朱安同往呢!可她有顾及,她担心儿子和许广平不会欢迎朱安这位名义上的“原配夫人”。鲁迅一直不待见朱安,在他眼里:她仅仅是母亲的一件礼物,而已!也正因此,数年前,他才会孤身南下,并毅然冒着被天下人唾骂的风险,与许广平同居。
思来想去后,拿不到主意的鲁瑞决定写信去探探口风。于是,她让俞芳代写了一封信,信里她表示:自己想来上海看望他们,只是一个人行动不便,需要在与俞芳同行的同时,带上潘妈(家里的佣人)。
鲁迅很快回信了,信里,他说:有俞芳伴送到上海是再好不过的。但是不能带旁的人,因为一来南北言语、习惯不同,旁的人到上海,未必能发挥作用。
鲁瑞听明白了:儿子是在告诉自己,此次前往上海,只能她一个人和俞芳前来,其他的人,一个也不能带。
收到信后,鲁瑞心里咯噔一下,这个结果是她意料之中的,可当这个结果展开在她眼前时,她还是有些难以接受。
之后的鲁瑞开始做甜干菜,她还亲手晒发芽豆,她似乎准备与俞芳前往上海。可是,临近出发时,她却很“凑巧”地胃不舒服了。她对俞芳说:
“医生让我不要出远门,不可过度劳累,上海我暂时不去了。做的这些菜,我到时候邮寄到上海便是。”
俞芳心里有些纳闷,毕竟:她眼前的太师母鲁瑞,看起来和平日并无两样。但她并没有劝说鲁瑞与自己同往,她觉得那样做有些冒险。

鲁瑞与俞家姐妹(1929年;左二为俞芳)
后来,回忆起这段过往时,俞芳曾带着内疚说:
“如果我劝太师母冒险和我一起去上海,她老人家看到大先生、三先生两家人,祖孙三代团聚。太师母晚年生活必然过得充实、热闹而富有生趣;大先生的身体,在太师母和广平师母的悉心照顾下,寿命或可延长几年,然而……”
俞芳之所以会这样说,显然是因为:她不了解鲁瑞和朱安的感情。此时的鲁瑞与朱安,已经相依相伴30多年了,她们早已情同母女。
就在俞芳准备前往上海与父母团聚前几天,鲁瑞在经过朱安房间时,竟看到她在揉眼睛。鲁瑞以为朱安在哭,她心里难受极了。她下意识地想:若自己这一去,就不能再回来了,朱安怎么办?
朱安一直依靠鲁迅给自己的赡养费过活,她若真去了上海,儿子是否会按时给朱安打生活费呢?若不打,她又怎么生活呢?
鲁瑞同时也想到了另一个问题,没有朱安在自己身边照顾,她能适应上海的生活吗?若是适应不了,俞芳又不回北京,自己又该怎么办呢?
正是基于这些,鲁瑞不得已放弃了前往上海与子孙团聚的机会。
一年后她才知道:自己竟就此错过了与长子鲁迅的最后一次会面。
俞芳南下后,鲁瑞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各种吃食邮寄了过去。她想着:自己没来,他们能吃到她亲手制作的小菜,也是一种安慰。
鲁迅并未在信里详细询问过母亲未南下的缘由,鲁迅不用问也知道:“她不来,定是因为顾及朱安”。长久以来,朱安一直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一道墙,只要这道墙还在,他们母子便不可能像普通母子那般“心连心”。
鲁迅对母亲过分在意朱安感受的行为很不理解,早在1932年,鲁迅最后一次北上探母病时,他就对母亲的一些行为很不满。
当年11月9日夜,鲁迅接到电报——电文云“母病速归”,11日晨,他急匆匆从上海北站登上 北去的火车,马不停蹄地赶回曾住过两年多的北京西三条旧寓。母亲那次的病并无大碍,可这次探病后,鲁迅的“心病”加重了。因为,他发现母亲竟把其他孙儿的照片挂在墙上,唯独不挂自己儿子周海婴的。

周海婴31个月
鲁迅当然知道母亲并不是不爱周海婴,他明白:母亲不挂海婴的照片,全因为顾及朱安的感受。
他心里很不平:母亲为了她,就可以完全不顾儿子和孙子的心情了?
鲁迅并未就此事详细询问母亲,但他盯着屋子里的照片看时,鲁瑞已经明白了:她是介意的。鲁瑞并没有解释,也没有告诉儿子“海婴的照片我放在枕头底下了”。
母子俩这最后一次见面都有些膈应,可他们都是不喜欢解释的性格。于是,双方的隔阂便也越来越重了。只是,隔阂归隔阂,它并不能影响母子之间的深厚情谊。都说了,血浓于水。
鲁瑞拒绝前往上海,鲁迅心里也有介意,但他依旧不问,鲁瑞也并不解释。他们之间一切如故,往来信件里,母子俩依旧只聊家长里短,偶尔,他们还聊聊老三周建人。在1935年12月21日的信里,鲁迅曾写道:
“老三因闽北多谣言,搬了房子,离男(我)很远,但每礼拜总大约可以见一次。他进来身体似尚好,不过极忙,而且窘,好像八道湾方面,逼钱颇凶。”

鲁迅故居
1936年起,鲁迅给母亲的信里,除了聊儿子周海婴的“成长烦恼”外,聊得最多的就是:他自己的病情。
鲁迅突然频繁在信里聊自己病情的举动,似乎很有深意,他似乎在提醒母亲:我的身体不行了,可能会走在你前头,你要有心理准备。
7月6日的信里,鲁迅对母亲说:
“不寄信件,已将两月了,其间曾托老三代陈大略,闻早已达览。男子五月十六日起,突然发了,加以气喘,从此日渐沉重,至月底,颇近危险,幸一二日后,即见转机,而发热终不退。”
此时的鲁迅已经被确诊患有严重肺病,他每月都要发病两次,他还曾经生过一次重症肋膜炎。鲁迅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,他甚至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。此时的鲁迅,自然比平日思绪更多了。
在与母亲的往来信件里,他的话也较往常更加细碎了。在其中的一封信里,他似无意地写到:
“我的一切朋友和同学,孩子都已二十岁上下,海婴每一看见,知道他是男的朋友的儿子,便奇怪地问道:‘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呢’?”
鲁瑞看到这段话后,反反复复琢磨了很久,或许,儿子并没有别的意思,但因为她自己心里有愧疚,她总觉得:儿子这话,似乎是在责备她这个做母亲的。
“如果我没有装病把他骗回来,逼他娶她,他兴许就跟他的朋友同学一样,早就有儿子了。都是我,害他快50岁才得了一个儿子,哎!”鲁瑞嘴里喃喃念着,心里如针扎一般地难受。
鲁瑞清楚地记得,儿子被骗回来结婚后的第二天,家里的帮工就告诉她:大少爷的枕头都湿了。鲁瑞也清楚地看到:儿子一边脸上有靛青,那是枕头掉色后沾在脸上的印记。那一刻,她才知道:自己做了一件错事。

朱安与鲁迅
也是从那以后,鲁瑞决心:不再介入儿子的婚姻,所以老二和老三结婚生子,都是他们自己的安排,她从未插手过。
鲁瑞毕竟不是一般的老妇人,因为幼年时旁听过一年私塾,又自学了很多知识,她也算个小小的文化人。所以,她是明理的,她甚至支持儿子用笔做斗争,哪怕这样做会面临各种危险。
鲁瑞甚至还剪短了头发,并在很早以前就学着年轻人放了足。可偏偏,她知道变通,儿媳却一直死守着传统。鲁瑞一想到朱安不肯听鲁迅劝告“放足”、“进学堂”,她心里就止不住地哀叹:真固执啊,真固执啊!
可鲁瑞也知道:自己的儿媳,除了固执,没有别的任何毛病。她对自己更是一顶一的孝顺,这几十年来的尽心伺候,就是明证。
好儿媳,却不是好太太,鲁瑞曾为了让朱安有机会成为“好太太”做过努力,她让朱安给鲁迅做这做那,甚至让朱安给鲁迅缝过棉裤,可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了。
好在,无论鲁迅多不待见朱安,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依旧很好,似乎从未有过隔阂一般。可真的从未有过吗?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一个毁了儿子一生幸福的母亲,怎么可能母子全无隔阂呢?若真的全无隔阂,自己到了这把年纪,怎会享受不了天伦之乐呢?
不过,鲁迅终于还是有“后”了,虽然他得子时已经48岁了,可终究也是“有后”了。鲁瑞不敢想象:若儿子一生不曾留下任何子嗣,她心里该有多过意不去。
鲁瑞早就通过儿子在信件里的絮叨听出来了:儿子很爱海婴。有时候,一封信几百字,竟全是在说海婴。他什么时候变长了,什么时候捣乱了,他通通会在信里告诉她。只在听儿子讲海婴时,她心里是欣慰的。
可一想到海婴一出生,儿子就已经老了,她心里就很不是滋味。

周海婴幼年照
当晚临睡前,鲁瑞一直在想回信的事,没错,她想在信里安慰儿子一番。可第二天提笔回信时,她完全没有提及相关,信里,她只叮嘱儿子注意身体,顺带聊了北京的物价和新看的小说。
这之后,鲁迅在信中越发频繁地提及自己的病了,9月3日的信里,他写道:
“男确是吐了几十口血,但不过是痰中带血,不到一天,就由医生用药止住了。男所生的病,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,其实不是,而是肺病,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。”
鲁迅和母亲写信从来没有避讳,他继续补充说:
“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,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,躺倒过的,就都是这病,但那时年富力强,不久医好了。”
鲁迅补充的这句话言外之意是:以前年轻,倒下了能起来,现在却不好说了。如此明显的提示,鲁瑞定是听明白了。
鲁迅这次躺倒后,一直医了三个月,期间,药更是没停过,可无论怎样,他的病也依旧没有好转。
写完这封信仅仅半个月后,病入膏肓的鲁迅再次提笔给母亲写信,这封信,也成了他给母亲最后的绝笔,汇报完自己的病情后,他写下了一段话,这段话再次刺痛了鲁瑞:
“海婴同玛利很要好,因为他一向喜欢客人,爱热闹的,平常也口出怨言,说没有兄弟姊妹,只生他一个,冷静(冷清)得很。”
敏感的鲁瑞不可能不想到:儿子似乎是在借海婴之口抱怨自己孩子太少了。是啊,她活着的三个儿子,个个都有几个子女,唯独长子鲁迅,年近半百才得了一个儿子,哎!
许广平与周海婴(鲁迅寄给母亲信中夹带照片之一)
鲁瑞一面替儿子的健康忧心,一面再次陷入了自责。她对儿子始终抱着亏欠,她对儿媳又何尝不是呢!鲁迅好歹还有个子嗣,可朱安却生生守了一辈子活寡,且没有任何子嗣。
“哎!”再次长叹了一声后,鲁瑞将儿媳朱安叫到了床边,她轻轻道:
“大先生怕是病得重了些,他信上说‘再过一星期停一星期药看一看’,我还是不大放心,你也要有准备……”
朱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,但半晌后,她又闭上了嘴。她可能想提议“去上海看看大先生”,可一想到自己的出现可能会让许广平等人尴尬,她又觉得不妥。或许,她只是单纯想对大先生的病说一句什么罢!
朱安的欲言又止,让鲁瑞心里更加难受了。当晚,她彻夜未眠,她总觉得儿子的病要不好了。
果然,这之后不到一个月,鲁瑞就得知了儿子的死讯。
整整六日,鲁瑞都没有哭出声来,朱安并不敢当着婆婆的面哭,但鲁瑞已经从她肿大的双眼知道她一定偷偷哭过了。那几天,鲁瑞走路已经不稳了,她每走一步,都需要朱安搀扶着。

鲁瑞老年
鲁迅去世的第七天,鲁瑞终于忍不住哭了,她边哭边对人道:
“端姑死得早,太先生卧病三年,他的逝世总有些想得到的。老四(椿寿)死了几十年,至今我还常常想到他,老大是我最心爱的儿子,他竟死在我的前头,怎么能不伤心呢?”
鲁瑞这样哭诉时,朱安只在一旁不住地用手抚摸着她的后背,以给她安慰。这些日子里,她的心里也分外难受,她和鲁迅虽早已是有名无实的夫妻,可在她眼里:他一直是她此生唯一的夫君。如今他走了,她又怎能不伤心呢!
或许是朱安的安慰起了作用的缘故,鲁瑞竟在喘了几口气后,似自我安慰一般地道:
“论年龄,他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,也不算短寿了。只怪自己寿限太长!如果我早死几年,死在他的前头,现在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。”
鲁瑞并不知道,离世前,鲁迅曾数次欲言又止地看向许广平,他似乎想交代什么,但终究什么也没说。

鲁迅生前最后一张照片(摄于1936年10月2日)
没人知道鲁迅未出口的“交代”究竟是什么,但他死前定然会想到母亲,毕竟,母亲在他的一生中,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。他的众多作品,如《社戏》、《故乡》等等,都有提及母亲。他的笔名,甚至也用了母亲的姓。
可叹,鲁迅对母亲的情感却终究“复杂”,这种复杂,从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便可见一斑。
鲁迅早期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是慈爱、宽容的,《社戏》里,“母亲以她慈母的情怀护佑着他稚幼的身心……”
然而,鲁迅后期作品里母亲的形象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,此时的母亲形象大多表现为:为病入膏肓的儿子从大仙那里求得“保婴活命丸”,为死去多年的儿子迁坟重葬等。
这些描写无一不在透露母亲的愚昧无知和残忍,母亲爱着子女,却完全用封建礼教的旧思想、旧眼光看待自己子女。此时的母亲,已经不是早期用爱为子女撑起一片天地的母亲了,此时的母亲,逐渐转变成伤害子女的刽子手与“毒药”。
鲁瑞当然不知道:儿子是在用文学发泄着他的不满。鲁迅不想让母亲知道,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,只让它们在文章里爆发。
他的压抑背后,是对母亲深沉而真挚的爱。
人世间的事,是没有圆满的,鲁瑞和鲁迅这两代人之间的鸿沟,是他们永远无法填满的“缝”。可幸运的是,再深的缝,在“骨肉相连”面前,也仅仅只是“缝”,它终究没有阻断母子之间爱的流动。
鲁迅去世7年后,年85岁的鲁瑞辞别了人世。离世前,她一直反复对朱安絮叨说:“我走了,你怎么办呢?”
可叹,鲁瑞离世前,心里最挂念的依旧是长子的原配妻子。她对朱安的放心不下,折射出的:谁说不是她对长子满满的爱呢?!